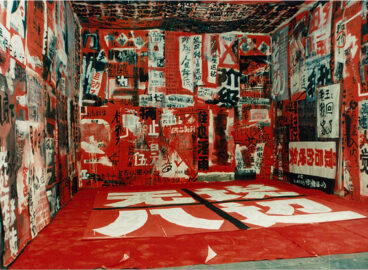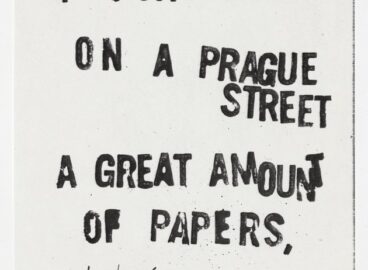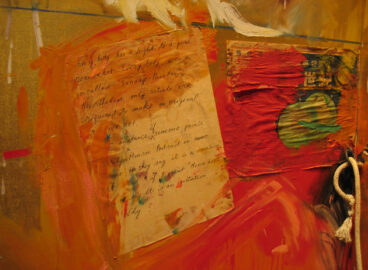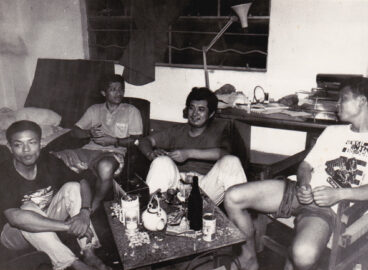Of Stone and Sand: John Cage and David Tudor in Japan, 1962
John Cage and David Tudor visited Japan in October 1962 at the invitation of the Sogetsu Art Center (SAC). Over the course of the month they gave seven concerts in Tokyo, Kyoto, Osaka, and Sapporo, causing a sensation that would become known as “the John Cage sh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