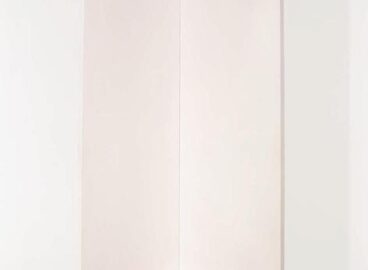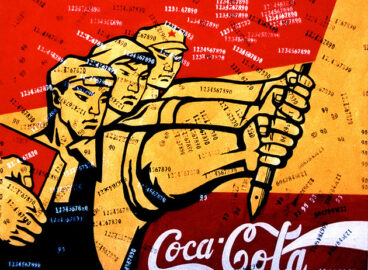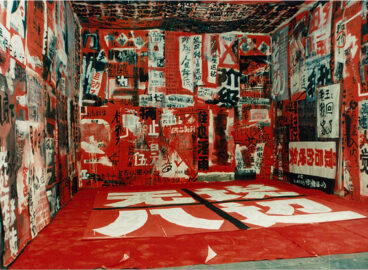Cildo Meireles’s “Virtual Spaces”
Assistant Curator Lilian Tone reflects on the origin of Brazilian artist Cildo Meireles’s Corners series. Virtual Spaces: Corner 1 (1967–68) simulates, with a twist, the corner of a domestic room, complete with parquet flooring, a painted baseboard, and canvas-covered walls. It is the first of a series of works that marked a breakthrough in Cildo…